
|
男性cp患者依旧想着嫖,看的时候一直不禁在想女性cp患者遭受到的不公是不是更多,身体上的无力是不是使她们更加无法对抗外界的恶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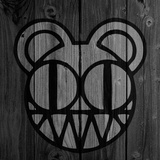
|
粗糙,生猛,激烈,极端主观,有争议性的拍摄方式。以"特写长镜头+摇晃的手持摄影+粗颗粒画质+音画分离" 的形式營造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影感受:一是超现实的夢幻感-以“橘子园”那场戏最爲精彩,通過聲畫分離製造疏離感,讓人產生幻覺,手持長鏡頭的使用加深了幻覺,鏡頭在各種cp患者之間游走,將觀衆置於如伊甸園般的夢境中 。二是极端不舒服的观影体验,cp患者的大量特寫長鏡頭配以不同步且口齒不清的患者自述,給觀衆強烈的壓迫感,目的是進行角色置換,讓觀衆感受到cp患者被正常人觀看的不舒服。Yokota全裸跪在路中間並直視鏡頭的畫面簡直就是對所謂正常世界正常社會伸出的中指。影片結尾Yokota在馬路上匍匐掙扎,清醒的意識到自己根本無力改變現實,整個影院都被這強大的無力感和絕望感所籠罩。 |

|
听他们含糊的说话,几乎没有听明白的时候,几十分钟的电影都觉得厌烦,简直难以想象如果日复一日和他们的日常接触。他们说着性,说着「人的权利」,但事实上根本是得不到的吧?最后裸体展现的姿态,在柏油马路上爬行的神情,含糊不清地表达着自己追求的「正常」。这样的活着,是一般的「活着」吗? |

|
影评里看到“影片的第一个镜头男主人公爬着紧张过马路的镜头是答应拍摄的人生第一次爬行过马路”,原来如此,难怪这段开头看得泪流满面,下作残酷又悲哀,我是说导演。他们并非演员出于身体缘故被记录的只有(除导演怂恿外几乎)真实呈现,任人宰割,而导演也确实好好宰割了一番,为了艺术和他的苦痛。居心叵测 |

|
一场感知与身体伦理实验。约定俗成的视听法则在原一男这里既有失效之死,又神奇地复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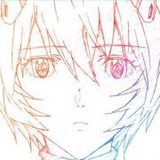
|
看完后脑子也是乱成一团麻。摄影很有新浪潮的感觉。做为纪录片,原一男对状态的记录很敏感,同时也是十足残酷。特别是用镜头将扭曲的面部通过特写放大,让CP患者们谈论他们的性经历,让我产生了一种几乎就要呕吐的陌生感。也不免疑惑,导演对于现实不虚饰而直面所表达的真实,到底意义何在?
最后的裸体应该是创作者的意图,用作对于CP患者,生存状态的一种影像提炼。很提神,很大胆,很恰当。 |

|
【导筒空间原一男作品展】原一男首部纪录片作品。是导演和脑性麻痹患者互相指导、互相争执,共同策划的“共谋”之作,也是一种身体力行的行为艺术创作。原一男在映后详细介绍了拍摄背景,坦诚几乎没有剪辑只是罗列拍摄素材。原一男鼓励横田弘等拍摄对象:要让城市变得对残疾人士友好、可以正常生活,残疾人必须把自己先“扔”到城市里。质问、反抗、打破城市所谓正常人秩序。因此原一男鼓励横田弘爬过人行横道。结果之惊险让两人都惊出一身冷汗,才知践行这种理念并非易事。结果社会秩序并未被轻易打断,反而引发横田夫人的心疼和反感,造成家庭矛盾。横田在激将法下坚持拍摄,主动提出去街头读诗。横田在新宿读诗是全片最震撼的高潮,被警察阻拦也恰恰揭露了健全社会对残障人士的暴力性。最后横田裸体坐在路上试图做高难动作,目的是拍摄到此为止。 |

|
原一男的拍法其实很特别,他的镜头不断在被摄对象和外部环境之间游走,以展现特殊生命个体面对外在理性秩序时的不安定感。他在建立感性视角时,常常通过他与被摄者的互动、对话。而他的理性思考又建立在他毫不掩饰以摄影机作为武器来试探边界上,也许他的摄影机正在模拟旁观这些患者的人群,或是一种外部的审视。在后面他与患者的一些矛盾中,也印证了他自己在《纪录片格斗》中所说的:“被摄者和被拍者是一种搏斗关系”。 |

|
【TIDF】原一男镜头的勇敢可以直接杀死我的怯懦。他端端正正的凝视,他毫无保留的记述,那企图消灭残障阖家健全的乌托邦究竟是谁的乌托邦?那以禁绝了用膝盖行走来确认自身双腿存在的尊严究竟是谁的尊严?睁开眼看啊,张开耳朵听啊,直到泪水让视线模糊,声音脱离画面嘈杂到无法听清,也请不要害怕地低下头去,无论是谁都有被注视的权利,在你的眼中他们才看到自己的存在。 |

|
脑瘫平头男的悲哀。海豹海狮一样行走。纪录片。人间行状。关爱残疾人。他们也是人,也想好好生活。他们的丑态比如不停摆头不是故意的。他们的孩子很正常。三星半 |

|
1、原一男纪录片处女作,异常生猛。2、是私密纪录片,也是剥削纪录片,原一男无视“纪录片伦理”,在被拍摄者抗议的情况下,仍强行拍摄。3、他们在谈论性经验的时候,就是在谈论我们共有的几乎无差别的欲望与体验——余秀华的“黄诗”,不足为奇。4、“扭曲”的、摇晃的特写,逼近我们。 |

|
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天然的反感和不适让我不断质疑导演的动机,随后我意识到,我们是这样被规训的,观看他们是不礼貌的,而原一男并不这样认为。从运镜到剪辑,这个话痨大哥真的是个天才。 |

|
纪录片的宿命是被观看,诚然,在观看这部片时,“观看”这一行为本身便作为了某种意义存在。拍摄者通过摄影机作为物理空间上的一道屏障,也是一种在自身道德上的规避——避免正眼直视“非人”,但一旦将图像置于一个多人的空间进行放映,“剥削”便不由自主地存在于某人的脑海。但看到最后,或许能意识到拍摄对象本身已从被观看者成为了意识-行动主体,因为观众了解到其作为人的——而不是非人的——(性)欲望、关系需求以及梦想。同时其多次干涉拍摄,已然成为了片子里外的主人。但我还是无能接受这种“假意示好”的本质上还是剥削的纪录片,除非拍摄者就是那位拿相机的人,剪辑也是根据他的意识而作的,否则我们只能根据影像拍摄时的主被动关系来代入早已设定好的情绪。 |

|
如果仅仅把它看作一部脑瘫患者生活实录就太浅显了,他的自白就是众生相。果园里那段一众残疾人的街访(居然侧拍也是残疾人),完全就是在讽刺工业化里正常人的人格异化,用纪录片的实录影像隐喻观众的现实世界,罕见又高明。技法上,作为纯纪实片,居然拍得特别主观,甚至比新浪潮时期的瓦尔达还要越界随性,非常大胆。我越来越喜欢原一男了,他的作品有种剔除一切浮华的野蛮生命力,豪放不羁,他在用镜头替主人公向世界竖中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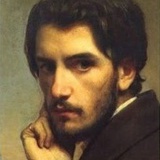
|
虽然是为了展现摄影机的暴力而做的,但看的时候实在是太难受 |

|
粗粝的,原始的,真实的。 |

|
It is the lethal and brutal social context, not the disabled body that needs to be rehabilitated. |

|
端着相机的横塚晃一在人来人往的路中央这段拍得真的和《丢掉书本上街去》英明在街上游荡的感觉非常像,六七十年代的人类真的好有意思,当年的映后非常激烈地讨论「解放障害者」的问题。青芝会还提出城市里必须有无障碍设施并进行过「占领」运动,这和同时期《残疾营地》里美国的残障活动家遥相呼应。关于青芝会的介绍: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E6%9C%89%E9%9A%9C%E7%A4%99%E7%9A%84%E4%BA%BA%E7%9A%84%E7%94%9F%E5%AD%98%E6%AC%8A%E9%87%8D%E8%A6%81%E5%97%8E%EF%BC%9F%E4%B8%80%E6%AE%B5%E8%BA%AB%E5%BF%83%E9%9A%9C%E7%A4%99%E4%BA%BA%E5%A3%AB%E7%88%AD/,还有立岩真也建的宝库网站“生存学研究所”(http://www.arsvi.com/)有很多资料(有中/英文版) |

|
导演在映后回应了对于摄影机暴力性的提问。摄影机在此片中是暴力的,毫无疑问。对于被拍摄者,拍摄者是有权力的一方,在残疾人的世界中,健全人的存在本身就可以是一种暴力。这种不对等处处都在,用温情脉脉的虚假平等,展示摄影机对被摄者关爱的眼光是有问题的。 |

|
错失大银幕(但早茶早茶真的好好吃!)前来补课,第一次啃生肉,手持摄影与音画分离,残酷的影像画面,极端的观点表达,直接的参与干涉,摄像机就是行使暴力的机器,主摄者作为健全人对于被摄者来说本身就是一种“霸凌”,大量特写带来的压迫感,畸形的躯体和囫囵的话语,没有轮椅只能用膝盖在地上匍匐,人于环境内是毫无依靠孤立无助的,高视角的俯视带有些许不可抹去的“蔑视”,而低视角下的运动又带有入侵的姿态,刻意的设置极端场景/空间带来刻意的生理上的不适观感,听着他在说话却始终无法沟通只能把话筒伸出,想读诗却被当成是一场freak show,再多的同情都因无法感同身受而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阳光照耀下的他们依旧没有希望仅仅是被看到,看着他拖着残躯,镜头随着身体的移动掠过,他在奋力前行,而我却浑身充满绝望和无力感… |

|
#WEB(9.4/10)
视线的暴力。几乎是革命性的反抗力量。人物在强力地向外释放能量的同时也在不断向内挤压、坍缩,和纪录片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构的,刺破现实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承受着从内部崩坏的风险。由此,残酷的痛感无论内外都维持着统一的高强度,只有分离的声画能让人稍作喘息。 |

|
人为什么需要区分自己和他人 正常和不正常 健全与。。。为什么需要区分 |

|
原一男故意将影像和声音放在不同轨道中,其导致的错位与差异,一方面在呈现眼前这些真实人物的困境,另一面则是在告知他们的声音被听到是有多困难。我们都是人,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善意和关怀。但人们的刻板印象和落后麻木的行为和鄙夷的眼神让这些残缺人更加难以存活,无论是生理心理。 |

|
很有学运色彩,包括最终失败的结果也是缩影的一种。和《略称:连环射杀魔》同一个时代的风景中,CP患者是另一种脱离社会正轨的人,只是他们无法高高在上地俯视一切。最动人的是原本只有原一男一直用摄像机侵入他们的方式鼓动他们也发起进攻,逐渐地其中一名CP患者也举起了摄影机反攻了回去,与作者和世界构成了对话。城市的风景绝不只是眼前的车水马龙和远方的钢筋混凝土,他们以身体入侵此处,以仰视的目光进攻日常景观,他们的历史也变得必须存在于这片地表。 |

|
和《监督失格》很像的,每次看原一男的东西,都会让我重新思考纪录片乃至电影存在的意义,思考影像所能表达的真实与虚构的模糊边界,还有导演所扮演的角色。前半段老实寻常,后半部分很感人很震撼,想了想,终究还是给了五星。 |

|
我還是無法認同原一男在此片的殘酷 |

|
或许导演就在忠实的执行纪录片的一个原则:“镜头要忠实的记录。越是不让你拍,就越是要坚持去拍。” |

|
看的过程中多次停下,看后心情复杂,对这一疾病的记录让我意识到我永远无法抗拒对某些疾病的偏爱和对另一些的厌恶。这是不是一场freak show取决于拍摄动机,如果是为了表现他们的生活那么ok,如果只是以此为武器去批判什么,那么我接受无能。对被观察的恐惧,拿起相机去拍摄别人,他说相机改变了我的世界。怜悯和排斥,对立又合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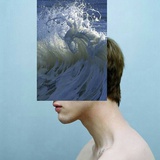
|
CP代表脑瘫患者,原一男在这部作品里就已经表现出他的纪录片一贯的冲击力,不舍不弃地记录所发生的一起,在所不惜。想起两件事,一是二姨小时候发烧成了半残疾状态,老妈曾说她是四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最后嫁给了比他大十几岁的二姨夫;第二件事是最近日本政府对1948~1996年间被政府强制执行绝育手术的精神疾病患者/遗传性疾病患者道歉并实施救济,不知道这些CP患者是否有受当年的政策波及,片中的几位患者死后都未受影响 |

|
导演说,拍摄是把身体残疾者从宗教保护者那里扔回社会,让大家真正认识到社会的体制性歧视,读诗、裸体,其实都是主角横田的主意。但原一男就生猛在,人家敢想,他就敢拍下去。 |

|
如此凛冽而不受控的力量体系亦存在巨大的内耗——要么摧毁周围,要么照亮周围。 |

|
原一男还真是不让观众尴尬就不死心。 |

|
对着空气打拳。因为原导演的电影逻辑是回答他自己的问题,探索自己内心(见他和Moore的对谈),所以很难触动50年后社会议题发生很多变化的观众的我,但是方法可以学习。想起来木樨园桥上断肢的残疾人,每次路过都借着我还没有挣钱,一定有机构层面的帮忙才能维持下去(确实是如此残忍的想法),所以没有帮助//读完Camera Obtrusa章节不由得反刍影片的方法,反思和系统合作的automatic reaction是否太犬儒。这么想想影片确实先锋和大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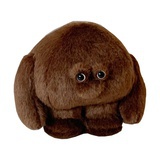
|
to disturb the comfortable,但是comfortable的到底是谁?average people?"the masses"?authority?disturbing的代价又是什么? |

|
绝对冷静,也绝对冷酷,修饰和伦理必须被摒弃,唯一路径是直接并且鼓励直接,于是记录本身成为目的,也成为意义。 |

|
Visibility matters. 如果凝视不再具有压迫性,主人公们的身体和与尘土齐平的姿态也就不再像是革命宣言。(看的时候想到新桥恋人里德尼拉旺用额头在马路上摩擦) |

|
看完很意外地没什么感想,可能因为我是一个outsider?
一些主观上对人物的喜恶(不涉及影片):被纪录者的大男子主义并没有因他们的身体缺陷而削弱,可能这是我无法同情他们的原因。那个曾经做过gangster的男子一脸自然地说出他曾强奸过一个女孩,让我明白他们本质上和身体健全者是没有区别的。人类是如此的stable啊。 |

|
上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看的,老实说,过程十分煎熬。但还是有些许震撼。 |

|
尽管项目本身是青草会要求的(这也免除了一些道德责任),但还是令人好奇原一男在一些场景设置中起了多大作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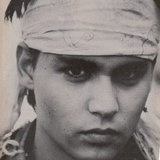
|
只看了最后二十分钟,手法观念超前 |

|
3.5分。非常野蛮而生动的纪录片。围绕着残疾群体的性、爱和被看见的梦想。每一个生命都有强烈活出精彩的欲望。关于伦理部分没有特别想清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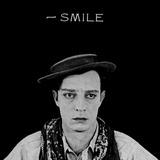
|
「附近映像季·广州」越到后面越不忍心看下去,这是拍摄者对被拍摄者的施虐和剥削。无法知晓导演是否是为了让观众同情被拍摄者才刻意为之这种残酷,但无论出于何种意图,都不应该如此超过伦理界限。//映后询问了导演,他解释摄影机暴力性的介入是他故意为之。他认为电视能看到的纪录片里所谓的平等是一种矫揉虚假的呈现,对残疾人来说,健全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他采用这样的方式目的是给被拍摄者一种反抗的力量。在他第二部作品里,他就有往回收,呈现的则是受虐性。 |

|
非常良心的电影,在制度健全的日本社会,尚且存在着很多黑暗中生活的人,那些被我们认为的“正常”意识下,被排除在外的人。导演将镜头对准一个这样的群体,他们有童年、有精神和肉体需要、有情动,渴望被理解和包容,奋力向前活着。我们呢,我们呢,我们尚未健全的体制下,新闻里看过的精彩片段都是,为了搞绿化工程,把盲道肆意更改,对铺张浪费冷漠脸的不在乎,轻视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健康问题,忽略留守老人们的精神需要!我们如何去面对现实的这些,如何建设性的改变态度呢。 |

|
"All these heartless problems of the human race sadden me very much." / 承认作品厉害 也承认自己无力接受这种残酷直白 一个患者说「跟导演在一起时 他一直在拍 damn him」 |

|
我旁边的姑娘哭成了泪人儿。 |

|
“为什么我不能拍照,不能是拿相机的那一个?我把相机对准其他人的时候,他们都会移开视线” 健全人怕看到他们,他们就应该躲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吗?残疾人即使不方便也应该多出来,这样公共服务系统多面对卡顿才能不断完善。 |

|
4.5星。看到过程觉得很煎熬,很漫长,但这两个词我认为对于这部片是褒义的,正是这部片想要达到的效果。大量俯视镜头,将cp患者的无助展现的淋漓尽致。最后念诗以及裸身的镜头仿若神来之笔。没有人想永远依赖他人,他们却只能靠着他人的同情活下去。接受自己是弱者,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也很喜欢患者们描述自己性欲的部分。
其中一个患者拿起相机,从被凝视到反凝视。
扣除的0.5星源自突如其来的英文配音,真的无比出戏了。 |

|
残酷无情的摄像机,刻意错位的音画,最彻底的「纪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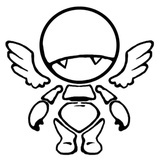
|
我们需要听到“弱者”的声音,因为只有他们会指出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不会想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我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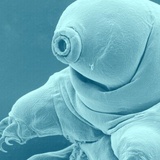
|
‘别光怜悯我们,我们也有话要讲’ 这也只是不可能实现的梦。当时看完这片 沉重之余生出愚蠢至极的励志感: 那我也能。实际谁与谁都互不相通 你本身还是你唯一的世界,尝试对自身之外的存在传达任何讯息,要么无法传到 要么仅仅以他们愿意的形式留存下来了,他们也许以好奇的形式在意过你,但它短暂,并且再次:你只会以他们愿意的形式占据他们一小部分的脑容量。科普有益,传达无用,绝对无用 |
![豆瓣评分]() 8.1 (188票)
8.1 (188票)
![IMDB评分]() 7.7 (179票)
7.7 (179票)![TMDB评分]() 7.60 (热度:0.99)
7.60 (热度:0.99)























